凤凰艺术 2021-01-18 07:44
原标题:文化之后的艺术:欲望、快乐、衰老和进化……

▲ Nanni Balestrini, A Fare Scandalo, 1960年。纸上拼贴。图片由Michela Rizzo画廊和Eredi Nanni Balestrini画廊提供。
“精力充沛是永恒的快乐。”——威廉·布莱克
先从欲望和快乐开始。我最近发现,在某个地方——我不太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吉尔·德勒兹讲述了他和米歇尔·福柯之间的一段对话。在离开德勒兹的家之前,福柯以他的风格,温和而羞涩地告诉德勒兹:我必须承认,"欲望(desire)"这个词让我恶心。我更喜欢用“快乐(pleasure)”这个词,你同意吗?
德勒兹完全不同意。他对“快乐”这个词不屑一顾。事实上,1973年德勒兹在温森斯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了一些这样的话:“Plaisir, quel horrible et atroce mot. Qu’est-ce que ça signifie?Le décharge?”(快乐,多么可怕、残忍的字眼。这是什么意思?放电?)
两人之间的讨论揭示了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先前讨论的欲望的一个维度,这一点我一直都不明白。70年代末我在巴黎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欲望是调动社会能量的引擎,但是我根本没有考虑欲望和快乐之间的区别。直到去年,当我读到德勒兹和福柯之间的交流时,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区别。
当然,我们可以从让·鲍德里亚身上找到这种差异的解释,他是70年代和80年代巴黎的真正智者。德里亚说:欲望,没问题,对美好事物的欲望,但要注意,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都建立在永恒的欲望之上。
现在,在我晚年的时候,我(痛苦地)体会到了欲望和快乐之间的区别,并且我了解到,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基于无休止的享乐推迟,同时也是基于对欲望的永久性兴奋。虚拟资本主义(Virtual capitalism),我称为半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是对这两种情况的加剧,延缓了愉悦和令人兴奋的愿望。
另一个促使我意识到它们的不同之处的催化剂是身体上的感觉,就我个人而言,变老本质上意味着失去获得某些快感的能力,而欲望却继续不受干扰。从我个人的经历和它所暗示的更坏的情况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有趣,也更令人不安。这种欲望的永恒燃烧和无法获得的快乐之间的关系与当前的历史过渡时刻有关,与人类进化的当前阶段有关。
为什么老年人如此紧张?甚至难以相处( Cantankerous)?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它听起来是正确的。为什么老年人如此恶毒?
我有两个答案。首先与年老时神经元和突触的消失有关:处理信息能力的降低,微妙性的丧失,感性和经验之间关系的定义的丧失。第二,我们——我们人类,尤其是老年人——倾向于抓住生命不放,因为我们认为生命是我们的私有财产。这生活是我的,我不想失去这份财产。
对死亡的否认深深地铭刻在现代人的心中。随着世界白人人口的老龄化,这引发了一种类似社会精神病的现象,即老年人对剩下的一切咄咄逼人的贪婪:赤裸的生命,腐烂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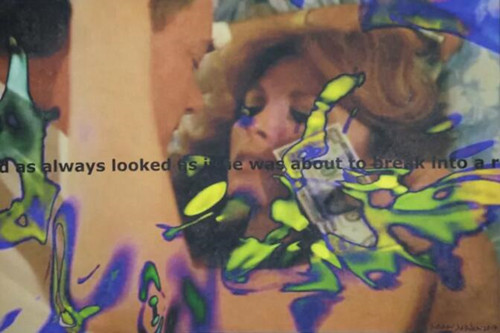
▲ Nanni Balestrini,Tristanoil, 2012年。由Galleria Michela Rizzo和Eredi Nanni Balestrini提供。
卡洛·罗维利(Carlo Rovelli)在其精美的著作《时间的秩序》(The Order of Time)的结尾写道,对死亡的恐惧是进化的错误。它是一种错误,因为人们无法思考没有自己存在的世界,无法思考没有我的世界。现代文化强调个人在与他人的持续竞争中,因此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集体感。因此,它把死亡变成了无法用思想、言语或精神阐述的东西。死亡被系统地否定了,这反过来使个体孤独地生活在无尽的悲伤沙漠中,最终无法看到个体与社会、我与你之间的连续性。
此外,现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能量的盲目崇拜之上的。它建立在对增长、扩张、生产力和加速的痴迷之上——对未来主义的痴迷使衰老变得不可想象。
为什么我要写这些奇怪又有点吓人的主题?我为什么要谈论衰老和死亡?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它们是我的问题。但是,相信我,这不仅仅是我的问题。它们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对死亡的否认,与对能量和扩张的盲目崇拜有关,已经把衰退和不增长变成了纯粹的负面趋势,把节俭变成了稀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已经变成了对时间流逝的偏执抗争。
我坚信,衰老是理解当前历史难题(看不见的或深不可测的)的钥匙,正如衰落是现代晚期危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第一,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情况是由人口因素造成的。现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口都面临着衰老的问题,并且不仅仅是西方国家。非洲人口成倍增长,而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人口稳步增长,西方的支配者和侵略者正在老龄化,他们正在失去活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失去对未来的天真信念,而这种信心主要来自年轻人。
南部大部分地区的人口爆炸与北部地区的人口下降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当代种族主义和侵略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老年人已经将其下降的力量转移到了战争机器上,而这些机器正在作为对南方被压迫者的永久威胁而发动,南方被压迫的人是试图向衰落的北方土地迁移的殖民地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就必须考虑衰老这一关键问题。
让我们想想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的复苏。唐纳德·特朗普,马特奥·萨尔维尼,鲍里斯·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弗拉基米尔·普京和雷杰普·埃尔多安。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吗?不,他们不是。这个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扩张的过程,是法西斯主义吗?不,它不是。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历史性现象。它是基于强大,充满活力的未来主义运动的意志力的运动。它涉及那些期待光明未来的人们,并促进了扩张,领土和市场的殖民化。现在没有人期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扩张不再可能,因为整个星球都被征服了,而市场已经饱和。领土空间的殖民已经结束,现在只能殖民时间。今天扩张的唯一方向是时间的强化和精神节奏的加速。只有认知空间的虚拟扩张和符号的加速流通才有可能。但这种强化正在摧毁人类的神经系统。
四十年前,我记得我和一些年轻的英国音乐家大喊:“没有未来!没有未来!”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前卫的挑衅。现在,每个人都认为未来已经过去。现在,这种情绪与大多数人所持的保守主义者立场相吻合。“没有未来”已成为常识,这就是为什么犬儒主义在当代文化,当代政治行为中不断扩大的原因。未来主义是对未来有所期待的社会的一种表达,是一个真正感受到社区温暖的社会的一种表达,无论是体现在国家、家庭,还是体现在与工人社区的社会联系中。所有这些都是100年前生活经验的现实。但不再如此了!今天,国家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国家的解体是信息数字化和以信息为基础的权力普及的结果。你认为谷歌属于美国吗?一点也不。美国属于谷歌的领土。意大利、法国也是如此,其他国家也是。
国家主权已经被权力的普遍存在所瓦解;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一种具有侵略性的身份认同形式,一种怀旧的愤怒。
归属感已经转变为一种无望的怀旧情绪,而这种怀旧情绪正是当代至上主义的根源。至上主义是老年人恐惧的一种表现。例如,正是因为他们害怕移民,才将其视为一种入侵。

▲ Nanni Balestrini,PLIS—Kaiser n7, 1989年。由Galleria Michela Rizzo和Eredi Nanni Balestrini提供。
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入侵。一两百年前,种族主义是白人入侵世界南部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种族主义是白人对自己领土被入侵的恐惧反应。伟大的种族“替代者”的种族主义偏执狂不仅仅是一个幻影,因为它符合一个真实的过程(一个在没有涉及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阴谋帮助下发生的过程)。感谢上帝,白种人正在消失。这是当代至上主义的根源,它既无能又超级强大;它无法改变一定程度上衰落的未来,但与此同时,它完全有能力以绝望的行动摧毁世界,其目的是重申一种已经消失的潜力。
“无能”这个词可以用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地球的北部地区。无能为力和复仇的欲望。新自由主义左派摧毁了对未来政治变革的任何可能预期。新自由主义左派:克林顿、布莱尔、达莱马斯、弗朗索瓦·奥朗德等等。这些叛徒已经摧毁了任何从政治和理性中期待有意义的东西的可能性。就理性而言,它已成为金融算法的仆人。当理性是一种财务算法时,我们能从未来期待的唯一事情就是复仇——实际上,是对理性的报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的序言中谈到了这种对理性的报复。他们写道,如果理性不能抓住它的黑暗面,理性本身无意识的黑暗面,那么理性就注定了它的毁灭。它已经死了。对理性的报复是正在蔓延的新反动运动的驱动力:这是对人类本身的报复。
人类作为一种文化视野已经成为当代非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敌人。他们是反人类的。对于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定义,因为他通过杀死经由地中海来到欧洲的人,建立了自己的财富。但请记住,右翼杀手萨尔维尼只是延续了意大利政府的政治态度,并实施了前左翼内政部长马尔科·明尼蒂(Marco Minniti)制定的规则。在萨尔维尼之前,他通过了法律,将在海上救援人员的非政府组织定为犯罪。萨尔维尼是一个名叫马尔科·明尼蒂的民主杀手的直接延续。因此,很明显,不存在摆脱这种情况的政治途径。
我们从这里去哪里?
我最近读了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与麻烦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当我阅读哈拉威时,我并不了解她的所有内容,但我了解要点。她以一种既讽刺又美丽的方式说,今天人们对科技有两种反应。一方面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技术将拯救人类、地球和环境。另一方是技术末日论者,他们说不可能,技术会摧毁一切。哈拉威采取不同的立场:她告诉我们要保持冷静。她说,人类注定要消失不是悲剧。
灭绝是当今政治舞台上的新流行词。看看在瑞典,在德国,在意大利,在世界各地的儿童组织的大规模游行。2019年3月15日,数百万儿童走上街头游行。他们传达的信息是关于灭绝。他们没有政治问题。他们只是说:到了恐慌的时候了。再看看灭绝叛乱。据我所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种族灭绝成为政治抗议运动的核心问题。
我不会集中精力反抗灭绝。有人可以反抗灭绝吗?我不这么认为。您可以应对灭绝。你必须应对灭绝。顺便说一句,灭绝并不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坏的事情。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导致灭绝的战争——不是死亡,而是金融资本主义为人类准备的持久痛苦。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将其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灭绝并不是那么糟糕。
在引用哈拉威之后,我想引用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家凯瑟琳·马拉布。她说,精神分析已经从性和语言的分析转变为神经学。性和语言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的焦点。但当我们谈到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或者恐慌症和抑郁症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不只是与性和语言有关的问题。它们关注神经学的物理层面。现在神经学正处于危险之中。是大脑,不是思想。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不只是思想,还有大脑。马拉布继续这个话题,写了创伤和神经可塑性。
从欲望和快乐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出发,必须从头重新思考进化。快乐是目标,是愿望。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因为沉迷于欲望而忘记了快乐,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摆脱资本主义的道路是相反的:出路不是欲望,而是快乐。大脑如何在当下找到快乐的新平衡呢?这是我们在未来几年,未来十年将要面临的问题。
我想把这篇前后不一致的文章献给一位于2019年5月去世的朋友。这个朋友叫南尼·巴莱斯特里尼。南尼是一位诗人、小说家,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重新组合者。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写过一个字的诗人。他拒绝了写字这种肮脏的工作。他问: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写文字?我是一个诗人。我不写字。我从各种信息渠道,从人们在地铁里的日常对话,从报纸,从广告中寻找迹象。他说,他的行动是重组。重组也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启示。但问题是:什么重组?意义的重组,语言的重组,欲望的重组,快乐的重组。诗歌是对现存事物的持续和有意的重组,目的是创造尚未存在的事物。
(文章来源:https://www.e-flux.com/journal/106/312516/desire-pleasure-senility-and-evolution/)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凤凰艺术”的所有作品,均为本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如需获得合作授权,请联系:xiaog@phoenixtv.com.cn。获得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凤凰艺术”。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