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作者:王纪宴2020-09-04 14:33
原标题:与其听《田园》不如看日出?
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有一个关于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广为流传的观点,即亲眼观看日出比聆听《田园交响曲》更有收获。这种观点很适合当今那些将身临其境的体验看得高于一切的“驴友”的口味。在这样的思维中,听《田园交响曲》——不管是听录音还是听“更真实”的现场,正如看风景画和阅读游记一样,都不过是与真理相隔一层的“非真实体验”,因而相对等而下之。真的是这样吗?
德彪西:《田园》像一幅劣质油漆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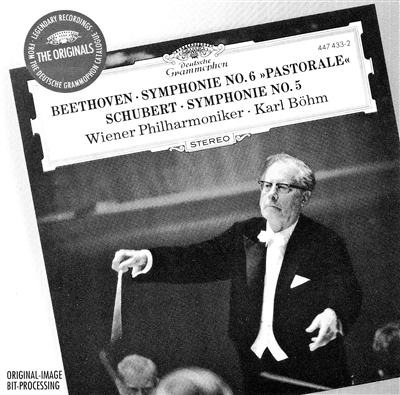
贝多芬《田园交响曲》 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
德彪西的这种说法来自发表在1901年7月1日巴黎《白色杂志》上的一篇《与克罗什先生的谈话》,这是德彪西虚构的自己的替身代言人“克罗什先生”首次现身。开篇为“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决定什么都不去做……”这是我们在后来以克罗什先生命名的德彪西的评论集中经常会遇到的情绪表达:什么都不想做,或什么都不想听——我们是否可视之为法兰西式的休闲心情,或是德彪西式的不那么想被他从事的音乐吸引因而沦为为职业所困的兴趣狭窄之人?在这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美好夜晚,有人敲响了房门,“长着一张精瘦又干练的脸”的克罗什先生走了进来。这位以“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自居的克罗什先生在和德彪西(难道这位著名作曲家不是“音乐行家”?)攀谈中,话题由巴赫转向贝多芬,先说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写得如何糟糕,继而将矛头指向了《田园交响曲》:
我更喜欢的是埃及牧羊人用牧笛吹出的几个音符,他让音乐与风景相结合,让我们听到的是你们那些理论书全然不知的和声。音乐家只会去听精心创作的音乐,却从不去听大自然中的声音。看日出对一个人的好处远胜于听《田园交响曲》。
这篇对话后来收入德彪西的文集《克罗什先生及其他》中,在2018年出版的《德彪西论音乐——反“音乐行家”的人》中文版中可以读到。而中国读者更早通过中文读到此文,来自与克罗什先生极相近的另外一种译法:克罗士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由张裕禾翻译的《克罗士先生》,110页的小书,一度成为批判“音乐行家”即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利器。德彪西的观点和腔调与我们习惯的乐评文风大相径庭,一言以蔽之,曰怪话不断。不过——照今日的说法:“然鹅”——德彪西式的大胆怀疑和连珠妙语也随处可见。在第13篇《贝多芬》中,德彪西再次谈到《田园交响曲》,这次是评论一场由当时最知名的贝多芬指挥权威之一魏因加特纳与巴黎著名的拉姆赫音乐会乐团演奏《田园交响曲》的音乐会。德彪西——或者说,他那位“克罗什先生”或“克罗士先生”——将贝多芬这部交响曲比喻为一幅油漆画,“那上面朦胧起伏的山影是用十法郎一公尺的粗绒做的,树叶婆娑的树木是用烫发的小火钳夹出来的。”
从未听过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人如果先读到了这样讽刺挖苦的比喻,是否会在一种被德彪西引导的先入之见中产生对贝多芬这部交响曲的不佳判断?这种可能性未必没有。事实上,德彪西对《田园交响曲》的抵触并非随感,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观点,他认为《田园交响曲》没有资格跻身于音乐杰作之列。
德彪西的这种见解在当代杰出的钢琴家和音乐著述家查尔斯·罗森的名著《古典风格》中有更理论化的共鸣。罗森指出,与前辈大师海顿的更富有“田园性”的作品如清唱剧《四季》相比,贝多芬使得这种体裁类型更为粗糙和感伤,“仅是依靠贝多芬壮丽的抒情能量才弥补了这种微妙平衡的损失。”
“大自然爱好者”贝多芬
对于为数众多的音乐家与热爱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听者来说,德彪西与罗森的认识与他们心目中这部作品的魅力和价值相去甚远。在音乐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著述者之一、英国音乐家唐纳德·弗朗西斯·托维在他卷帙浩繁的《音乐分析随笔》中有对贝多芬作品的深入精湛分析。他经常在行文和注释中回击一下那些试图贬低贝多芬创作的人,有一次他干脆写道:“我奉劝那些仍对贝多芬大放厥词的人,还是放明白些为好!”在托维看来,对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完美的经典交响曲。就像贝多芬的每一部交响曲,海顿的大约40部以及莫扎特的至少7部出色的作品一样,这部交响曲包含了在任何其他作品中都不可能发现的特征。否则它就不是经典了。”
对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发出赞赏的还有最具权威性的音乐辞书《格罗夫音乐词典》创始编纂者乔治·格罗夫,他在1896年出版的《贝多芬和他的九部交响曲》中,对《田园交响曲》的细致分析不仅没有陷入在一些研究者那里难免会出现的使其研究对象显得枯燥乏味的情形,反而会在条分缕析中激发读者对贝多芬笔下音乐的更大的热情。在罗伯特·辛普森为“BBC音乐指南”丛书撰写的《贝多芬交响曲》中,他认定《田园交响曲》是贝多芬写到乐谱上的所有音乐中最精彩的篇章,这部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溪畔景色”的乐队配器所表现的诗意从未为后世任何一位作曲家所超越。
贝多芬是大自然的热爱者,他喜欢在维也纳近郊的乡村度过夏天,喜欢在静谧的林间独自散步,他的很多美妙乐思是在他置身于大自然怀抱中油然而生的。相比之下,不喜欢《田园交响曲》的德彪西至少在创作时更显示出“城市动物”的一面。1914年2月,他在意大利罗马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到自己在巴黎的公寓里无休止地工作,记者问他:“您不喜欢在安逸的乡下作曲吗?”德彪西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巴黎工作室的环境好极了,好到我不需要到乡间寻找清净……但不要以为我对大自然和美丽的风景无动于衷。”
贝多芬对大自然的眷恋,一如他对自由的向往一样强烈。关于这二者的关系,贝多芬的传记作者马丁·格克指出:“音乐的道德层面是不能忽略的。贝多芬用他的作品来贯彻他的生存理念……‘自由’和‘自然’这两个伟大的理念,在启蒙运动的传统中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常常是用一口气说出来的。1796年到1799年,在勃朗峰的蒙代弗尔特建造了一个著名的纪念亭,亭上本来刻有‘一个自由之友献给大自然’的文字。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能够超越一切异化回归到他的本性;大自然的创造意志赋予他高尚而纯净的气息,使他能深深地呼吸,并使他能找到对自我和对世界的正确态度。”
这种被认为与卢梭有直接关系的观念,在那个时代有其普遍性。正如玛丽安娜·巴希莱在《贝多芬和他的时代》一书中所分析的:“《田园》也可以被视为19世纪艺术家‘重新发现乡村’的一个标志。对于贝多芬,一如对于在工业革命之初居住于人口稠密的都市的同时代人,乡村不再是对于莫扎特和海顿所意味的尽力避开的出于义务的逗留,而是从身体到精神的需要对象。”
在贝多芬的9部交响曲中,第六交响曲《田园》在各方面都显示出独特风格。贝多芬式的激情澎湃为一种轻松悠闲的心绪和氛围所取代,这从第一乐章“到达乡间时被唤醒的欣喜之感”一开始就能立即感受到。由第一小提琴奏出的充满阳光的 F 大调主题被认为是交响乐文献中最轻盈的开头之一,听者自此便以这种轻盈的步伐,跟随音乐作一次愉快的乡村旅游。作曲家在这个乐章里好像是要我们尽情地同他分享抵达乡间时的欣喜感受。第一主题的片断似乎是无休止地重复着,构成这个乐章的主要基调,就像是林间的光影,变幻丰富,令人兴味盎然。法国作曲家埃克托尔·柏辽兹曾这样形象地描述这个乐章:“可爱的乐句令人欢怡,有如芬芳的晨风;成群的鸟儿从头上飞鸣而过,空气时时因薄雾而呈湿润;大片的云块把太阳挡住了,但顷刻之间,云块吹散了,林木泉水之间又突然充满了阳光……”
在英国学者辛普森盛赞的第二乐章“溪畔景色”,听者随音乐来到了小溪畔,聆听悦耳的潺潺流水声,随着蜿蜒的溪流前行。当走过一棵大树下时,听到夜莺、鹌鹑和杜鹃的啼鸣。柏辽兹对这一乐章的感受是:“作曲家创作这个可爱的乐章时,一定是躺在草地上,仰首观天,听着风声。光与影的交错诱惑着他,他注视着闪烁的微波,倾听着细浪拍岸的喃喃私语。这是何等的美景良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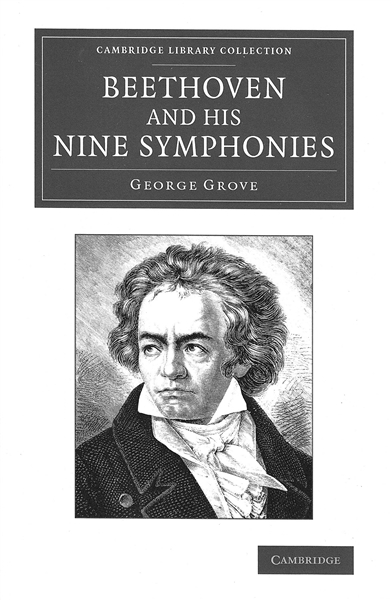

维也纳南郊的莫德林周围景色,这里是贝多芬在夏天喜欢逗留的地方之一
后三个乐章是连成一体的。在第三乐章“村民的愉快聚会”中,突兀的转调、听起来常常参差不齐的乐句以及对乡村乐师演奏的模仿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内心的丰富幽默感。对于这一乐章里由双簧管吹奏的舞曲主题以及伴奏声部里并不引人注意的大管音型,柏辽兹以他丰富的想象力描摹出这幅乡村画面的几处细部:“欢笑舞蹈的村民们起初好像还不十分热闹,这时有一支牧笛吹出了快活的副歌,一支大管在伴奏,它好像只会吹两个音。贝多芬一定是有意藉此来表现那善良而古老的日耳曼村民,他蹲在酒桶上,手里拿着他的残旧不整的乐器,只能从这乐器上吹出 F 调的两个主要的音——主音和属音。每当双簧管吹奏出牧歌风味的、单纯活泼得像是穿着节日新装的少女的曲调时,古老的大管便在一旁甩出自己的两个音,当旋律转了调时,它便停了下来, 默默地数着休止的拍子,直到它熟悉的曲调又回来了,便连忙吹出 F、C、F。这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效果,常常并不为听众所注意。”
在一阵不安的骚动之后,迎来了第四乐章“暴风雨”。雷声大作,闪电交加,暴雨如注,大自然充分显示了其至高无上的威力。但这是贝多芬这位理性主义时代作曲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它是仁慈的,它所施与人类的不是破坏性的风暴,而是惠及众生的恩泽。暴风雨很快过去,当最后一阵雷声在定音鼓上闪过后,长笛的一连串上行音阶让我们想到阳光照耀下晶莹的水珠。第五乐章“牧人的歌声——暴风雨过后的幸福与感激之情”,以单簧管吹出的模仿牧羊人歌曲的质朴曲调开始,引出小提琴歌唱的虔敬主题,这是对自然的礼赞,对上苍的感恩。这个主题在不断的变奏中和插部的映衬下显得愈发绚烂多姿,仿佛展现着浩瀚的晴空以及大地万物生机勃发的景象。
日出是日出 《田园》是《田园》
贝多芬在《田园》交响曲中所显示出作为作曲家的创造性,并非简单地体现为所谓“前无古人”的独创性。事实上,器乐音乐作品中对田园和大自然进行描绘的传统,在像戴维·温·琼斯这样的当代学者所作的详实学术考证中,可以一直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教堂音乐中就有大量与田园有关的作品。而维瓦尔第的《四季》,海顿的交响曲和清唱剧,是更晚近和广为人知的先例。事实上,贝多芬创作《田园交响曲》更直接的借鉴来自较贝多芬年长18岁的德国作曲家尤斯廷·海因里希·克内希特创作的《自然音画,或大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也由五个乐章构成,每个乐章也有标题。克内希特和他的《自然音画》长期被忽视,甚至在《简明牛津音乐词典》中都没有克内希特的词条。但情况在近年出现了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位“也创作了一部《田园》”的作曲家。2020年初,Harmonia Mundi唱片公司将柏林古乐学院以复古方式演奏的克内希特《自然音画》和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录音一起发行,这两部有着特殊关系的交响曲第一次联袂出现。而被评论家和听众认为演奏得更精彩的录音版本则是克里斯蒂安·班达指挥意大利都灵爱乐乐团的现代乐器版。
在对比聆听中不难感受到,虽然克内希特的《自然音画》也非常优美悦耳,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更内在深沉的艺术表现力明显为《自然音画》所不及。二者间的共同之处是对卢梭式的或者华兹华兹式的美好亲切的乡间大自然风光的表现。在当代思想家眼中,这样的大自然是被美化的,这一点其实也是德彪西所怀疑的。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所著的《乡村与城市》,引用诗人乔治·克雷布的长诗《村庄》中的诗句,来表达这种怀疑:
你们这些文雅之人,
梦想拥有乡村生活的闲适,
喜欢流畅的小溪和更为流畅的十四行诗;
去吧!
如果你们的赞美也包括安宁的茅舍的话,
朝里望望吧,问一问那里是否真有安宁。
但实际上,大自然虽然有其威严甚至无情的一面,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她永远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生存怀抱这一事实。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之后,作曲家们不断地以自己的音乐表现大自然的主题,英国作曲家沃恩·威廉斯也创作过一部《田园交响曲》,而马勒的《第一交响曲》虽然没有“田园”的标题,但其第一乐章表现大自然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却是表现大自然的最清新动人的杰作之一。
格罗夫的《贝多芬和他的九部交响曲》一书中列举了曾经有过的多次为《田园交响曲》配上画面演出的尝试,而最后的结论是:画面是画面,交响曲是交响曲。也就是说,贝多芬的交响曲中为我们描绘的田园,是一个容纳了我们每个人的田园记忆的独特的田园,那是任何画面都难以替代的。“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写道:“令人陶醉的景致通常让我们意识到语言的贫乏。”令人陶醉的音乐难道不同样让我们意识到语言的贫乏?德彪西关于听《田园》不如看日出的话其实没有说错,亲眼看到日出壮丽景象的感受是不可替代的,但,专注投入地听一遍演奏得最精彩的《田园交响曲》音乐会或经典录音——如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或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精神上唤起的愉悦和升华,所激发的对自然、对上苍的敬仰,对世间万物的热爱,也是看日出所未必能带来的。总之,日出是日出,《田园》是《田园》。
(图片来源于北京青年报及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