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作者:徐一超2020-05-19 09:55
原标题:博物馆日|精英的还是大众的?艺术博物馆的“公共性”张力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艺术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旨在发挥审美教育、文化治理等功能,这种“公共性”也正是现代博物馆有别于传统私人、皇室收藏的独特立意所在。然而,就博物馆的“公共性”立场和面向而言,艺术博物馆事实上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其展览对象——艺术与艺术品一度是精英、高雅文化的象征,这就与不同阶层、身份、知识背景的公众产生了程度不一的“亲和性”。也就是说,虽然艺术博物馆在理念和理论立场上与其他的现代公共博物馆一样坚持公共性,但在展览和观展的实践及其客观效果中,艺术博物馆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普通大众不易跨越的“门槛”。虽然艺术博物馆一度被认为是精神教益的“圣殿”,它在审美体验之外还能传达诸种知识,然而在实际效果上,究竟有多少社会公众能够成为合格、有效的“接受者”呢?艺术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是不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美好想象?
另一方面,艺术博物馆的展览诗学是一个对艺术品进行选择、排列、组织的“美学加工”过程,这一过程无可避免地有所取舍和偏向,这其实也和“公共性”这一立意有所背离。应该认识到,艺术博物馆的展陈空间不仅涉及“展览的诗学”(poetics of display),而且涉及“展览的政治”(politics of display)——也就是展览诗学中所暗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康德将纯粹的审美经验视作一种先天的、无功利的共通感,这似乎最能体现“美”的“公共性”,但这也正是康德的局限所在,后来的一些理论家都指出了审美活动与意识形态、阶级阶层身份、功利性等的关联。更重要的是,艺术博物馆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活动,作为一个机构整体,它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话语关系。这一切,都导向了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辩证法”。
因此,艺术博物馆的实际定位也就处在了精英性和公众性、“少数人”话语和公众权利之间。而随着晚近艺术博物馆向“文化综合体”的转向,随着其文化消费、文化娱乐功能的突显,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深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加上资金方面的压力,艺术博物馆甚至表现出迎合“游客”的倾向。这还是艺术博物馆应有的“公共性”吗?这种“公共性”是否正在向“大众性”滑落?
一、从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
(一)私人收藏与权威性
在现代博物馆诞生之前,cabinet of curiosities(奇珍室)、studio(研究室)、galleria(画廊)等私人性质的收藏空间并不对外开放,或是只向主人的亲友们开放。这类公共博物馆的“史前形态”大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知识空间”,它们在知识阶层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一道区隔彼此的屏障。这些最初的私人收藏空间往往临近卧室,有些的入口直接开向卧室,“收藏者能够像退入卧室那样隐休于他的研究之中”。到了17世纪,“画廊”(galleria)这样的空间形态开始出现了,人们可以在其中穿行而过,“这就和空间上封闭的‘工作室’的静止原则形成了对比”。文艺复兴以降,这类私人性质的收藏空间大多为皇室、贵族、学者等所有。
在私人性的收藏空间中,主人们大多会对藏品进行“玩赏”,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梅迪奇家族的成员之一皮耶罗(Piero di Cosimo de' Medici)身患痛风病,发病期间他就这样在收藏室内打发时光:
接下来的一天,他或许又会取出他的一些皇帝和古代贵人的雕像和图像,有些是金的,有些是银的,有些是铜的、宝石的、大理石的或是其他材料的……第二天他可能观赏他的珠宝珍玩,这方面他的收藏数量巨大、价值不菲,有些精工细琢,有些不经雕琢。他怀着极大的兴致把玩这些东西、谈论它们各自的优劣。接下来的一天,他或许会玩赏他的金制或银制的或其他材料的花瓶,夸赞它们的卓越品质和制作者的手艺。……人家告诉我他的收藏如此巨大,如果他把每样东西都看一看,得花上一整月的时间,而过了一个月再看第二遍,他又不会厌倦了。
主人对藏品的这种“占有”和“玩赏”其实和中国古代的艺术品“把玩”十分类似。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在古代中国,完全的占有和“与世隔绝”是欣赏一幅绘画的前提:“绘画不是被展览的,而是要在一位处于良好优雅状态的艺术爱好者面前打开;其作用是加深和促进他与宇宙的交流”,这样的艺术欣赏和沉思与公开的画廊氛围不相容。可见,私人收藏不仅仅是积累财富、打发时光这么简单,它还涉及深邃的思想意义和身份认同。
搜罗世间各种珍奇的奇珍室空间就像是宏观世界的微缩映射,它代表着收藏主体对世界的认知、对世界秩序的认知。而当世界的“全景”呈现在面前,为个人所有时,这也是一种对身份、地位、权力、知识的自我回味和自我确证。比如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曾拥有16、17世纪之交闻名欧洲的私人收藏,这些藏品折射出世界的缤纷多奇,起到了一种“理想而完满的棱镜”的作用,奇珍室的微缩世界反映了君主对自然、对世界的“君临”,表达的是一种“以微观方式笼括万有、便于君主据之、可以象征性地声称对整个自然和人类世界拥有统摄权的企图”。甚至可以说,奇珍室私人藏品的主人们是积极主动的创造者、参与者,他们有能力“理解并重现自然界的智慧”,在象征和比喻的意义上,他们也就控制了时间、控制了世界。

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
随着奇珍室向现代博物馆的发展,私人收藏逐渐有限地向特定的访客开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皇室的艺术收藏。据考察,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皇室收藏通常都被安置在宏伟的美术品陈列馆中,它们被用作官方的接待室,是国家的仪式性空间。在那里,统治阶层的富丽堂皇会给外邦的来访者和本国的权贵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一阶段的“类公共博物馆”只具有有限的公共性,而即使它们开放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也只是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有着相似的特征,并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认为,以宫廷礼节、权力象征物等为典型表现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公共性的社会领域,而“毋宁说是一种地位的标志”。在中世纪的文献中,“所有权”和“公共性”是同一个意思,而“代表型公共领域”正继承了这一特征。通过在民众面前的展示,“它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非民众”,也就是说,“代表性公共领域”是要为所有权赋予“权威”,为所有者赋予一种“神光灵气”,并居高临下地将它们投射、照耀到民众身上。可以认为,18世纪以前皇室的艺术收藏其实正发挥着“代表型公共领域”的这种标定权威、彰显权威的功能,这也就是早期私人收藏与后来的公共博物馆相比所具有的私人性与权威性的特征。
(二)公共博物馆的“公共性”理念
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浮宫向公众开放,这一事件真正揭开了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理念创生的帷幕。在卢浮宫中公开展出的艺术品多数是原先的皇室收藏,当时吸引了大量的公众。据研究者描述,在当时新创立的一周十日制下,卢浮宫五天接待艺术家、习画者,三天向普通民众开放,另两天清洁打扫。虽然在时间上仍然采取有限的开放政策,但在向公众开放的日子里,卢浮宫总是异常火爆,一些娼妓甚至也涌入博物馆,政府还在附近重新布置了照明。

卢浮宫
向公众开放的卢浮宫之所以创生了有别于私人收藏的博物馆公共空间,是因为展览的布置、意图,参观者的身份、地位等都发生了转变。通过将原先的皇家珍宝在一个民主化的公共背景下提供给“公民”(citizen)们“检视”(inspection),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和叙事方式诞生了。在新的国家叙事中,举足轻重的不再是君主,而是公民;他们既扮演着叙事中的“主角”(arch-actor),同时又是操控这一叙事的“上层叙事者”(meta-narrator)。更形象地说,参观艺术品的民众不再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被置于“权力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power),而是被视作国家公民,作为主体和受益者处于“权力的这一边”(this side of power)。他们不再被权力所统治、所震慑,而是积极认同于权力。
因此,以卢浮宫为代表的公共艺术博物馆与昔日的皇家艺术画廊相比,就展现了鲜明的政治意义上的区别。作为文化机构,它们都通过艺术表征的形式使国家的概念成为一个可见的实体,然而皇家画廊将国家标定为国王的领域,公共艺术博物馆却将国家(nation)标定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一个在理论上属于全体人民的抽象的实体。因此,公共艺术博物馆能够服务于启蒙和现代化了的统治者的需要,也能满足新兴共和国家的需要。18世纪末19世纪初艺术博物馆遍布全欧洲的快速涌现也就在艺术表征的层面证明了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除却政治意义,博物馆公共空间的创生及其所带动的艺术展览的流行也改变了贵族、精英阶层占有、把握艺术的特权,艺术对于业余群体、普通民众来说也成了“可及”的对象。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任何人都有权利对一幅公开展出的画、一本公开发行的书或是一出舞台上的戏剧发表评价意见,“展览馆像音乐厅和剧院一样使得关于艺术的业余判断机制化”,人们可以通过讨论去接近甚至掌握艺术。就艺术而言,它也摆脱了皇家、贵族的生活装饰、权威展示、社交表现等功能,“变成了自由选择和随意爱好的对象”。
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与特定的展览诗学模式紧密相关,私人收藏向公共博物馆转变的时期,其实也就是奇珍室的展览诗学向现代博物馆模式转变的过程:二者事实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面向公众开放的卢浮宫也以全景式的“艺术—史”叙事模式为主,这一展览诗学使得“艺术体验部分地民主化了,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都能学习分类的系统以及每个流派、每位艺术大师独有的特点”。因此,艺术博物馆要彰显理念、立场上的“公共性”,就不仅要敞开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还需要相应地对空间内部的诗学秩序、象征规则等进行调整和打理。
而也只有在“公共性”创生这一前提之下,艺术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才有可能得到发挥;只有首先让艺术品对公众“可视”,才能进而通过“艺术—史”的展览诗学赋予感官“可视”的展品以理性“可读”的教益。可以说,私人收藏无论被怎样细致地分类、组织、保存,其教育性都无法突显;而当藏品被置于公共博物馆之中的时候,它们也就被整合进了一个“宏大的教育工程”。只有当艺术博物馆真正成为公共性的空间时,通过开放的物理环境与特定展览诗学机制的配合,藏品才不再被认为是“激发少数人好奇心”(stimulate the curiosity of the few)的工具,而被重新认知为“教育大多数人”(instruct the many)的途径。
此外,不妨一提的是,在成为收藏、展览的对象之前,艺术品作为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共同崇拜的实用性对象:这种在共同体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是一种“公共性”的体现呢?可以认为,作为巫术、仪式、生活等的实用工具的艺术品更像是“代表型公共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权威的“神光灵气”“统摄”公众,这与公共博物馆“接纳”公众的“公共性”理念显然有别。
还需要追问的是,在实践及其效果中,艺术博物馆的这种“公共性”真的名实相符、无懈可击吗?
二、在区隔与同化之间:反思艺术博物馆的“公共性”
(一)艺术博物馆的客观区隔效应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博物馆都被视作充满精神力量的“圣殿”,但细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对艺术博物馆的这类描述和评价其实大多出自诗人、作家、艺术家等知识阶层之口。有学者意识到,在一些人眼中,艺术博物馆不过是“一个俱乐部和富人光顾、充满时代气息的社交场所”。
对普通大众来说,艺术品曾经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它们与宗教仪式、求爱及家庭生活、工作、娱乐等直接关联,能够丰富普通百姓的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当艺术从宗教、生活等领域中分化出来,当艺术品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以后,它们一度成为皇室、贵族的专属品,与普通百姓产生了距离。公共艺术博物馆产生以后,社会公众在物理空间上获得了接近艺术的机会,博物馆也希望通过公共性的开放发挥教育大众的功能,但在客观效果上,艺术其实仍然与社会公众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19世纪末,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就指出:虽然流行的观点是公众只要能够在摆满高大玻璃柜和各色美丽物品的宏大建筑里走上一圈就会变得文雅起来,但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公众而言,一座灯火明亮的博物馆只是一个散步的场所、一个灯火通明的休息厅,它带给人的启发或知识甚至比不上摄政街或霍尔恩伯街那些商店”。据调查,公共艺术博物馆开放伊始,参观展览的普通观众不少都会觉得枯燥乏味,回家以后也难以回想起相关的知识性信息。这与那些具有良好文化艺术修养的专业人士迥然不同:“我不懂青瓷,无法理解它独特的美,而专家们对那些展品却怎么也看不够,恨不得将展出的每一件青瓷盘子拿在手里抚摸一番。”在普通观众眼里,艺术展品或许就只是“画笔和凿子创造出来的无价之宝”,他们常常“无精打采地穿过大厅,根本无法欣赏任何一件画布或大理石作品之美”。据报道,有的美国游客还会揶揄维纳斯雕像的腰身过粗而且是八字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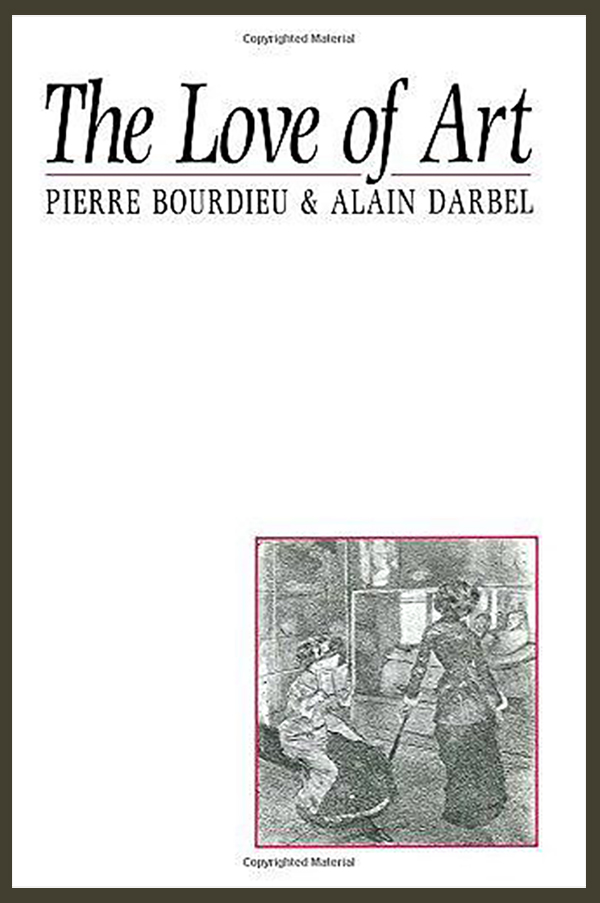
1960年代,布尔迪厄曾经带领研究团队对欧洲的艺术博物馆进行了经验性的调查研究,在《艺术之恋: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公众》(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一书中,他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论证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艺术博物馆在实际效果上对不同阶层民众的区隔作用,这项研究也成为后来《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一书的先声。布尔迪尔指出,科学观察和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文化需求是教养和教育的产物”,“所有的文化实践(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阅读等等),以及在文学、绘画、音乐上的偏好都与教育水平紧密相关,其次也和社会出身相关联”。更深入地说,对艺术品意义和趣味的感知要以某种“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为前提,而这种“文化能力”指的是熟知一套“用来为艺术品编码的代码”,因而对艺术品的解读也就可以看作是某种“破译、解码”的行为。而对于缺少这一能力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往往会“迷失在声音与节奏、色彩与线条的混乱之中”,“感受不到韵律或是情理的存在”。因而布尔迪厄认为,观看绝不仅仅是纯粹感官层面上的观看,“观看(voir)的能力就是知识(savoir)的功能”。具备不同“文化能力”“观看能力”的大众对于艺术品有着不同的接受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客观的区隔效应也就生成了。
布尔迪厄所谓的这种“文化能力”其实与丹托所说的“艺术理论氛围”(atmosphere of artistic theory)、“艺术史知识”(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art)十分相似,而正是这二者组成的“艺术世界”(artworld)使得艺术成为艺术。本尼特在提及艺术博物馆相关特性时所用的表述其实也是相近的意思,他认为,文化精英拥有的是一套“视觉能力”(visual competence)或曰“理论”(theory),正是依靠它们的媒介作用,艺术博物馆中的“可见”(visible)与“不可见”(invisible)之间才被建立起关联;这其中,“可见”的是展出中的艺术品实物,“不可见”的则是作为抽象认识范畴的“艺术”。可以说,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差别就在于能否“透过”(see through)可见的艺术品去感知那些本不可见的抽象的认知对象,就在于他们是迷失于纯粹感官的表象还是能够取得精神性的沟通。
艺术博物馆对观众的这种区隔作用,在现代艺术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格林伯格曾经举过一个“无知的俄国农民”的例子:如果让一个俄国农民在毕加索和列宾的画作间自由选择,会有什么结果呢?显然,列宾的画对他来说会更具吸引力,因为他能在那里发现“价值”——“可鲜明辨识的事物的价值,神奇的和富有移情特点的事物之价值”,“这位农民用辨识和观看画外之物的方式来辨识和观看列宾所画的东西,因此艺术与生活之间不存在断裂”。
已经为人所熟知的一点是,传统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反映生活、模仿生活的特征,现代艺术则力图体现“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性”,更注重艺术表征形式本身的特质。而就不同的艺术接受者而言,“比起被表征之物,知识阶层更加信奉的是文学、戏剧、绘画的表征形式本身;然而普通民众主要期待的,则是那些支配他们的表征形式和惯例能够允许他们‘天真’地信奉被表征之物”。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被表征的“生活”与“真实”才是他们乐于接受、能够接受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博物馆相对而言只能体现出较为有限的“公共性”,因为真正能够理解并感知它们的受众只会是具有良好文艺修养的群体。
可以认为,一度占据主流、采用“艺术—史”展览模式的“全景式博物馆”有着更强的“公共性”,它们通过历史主义的叙事传达社会历史知识与有限的艺术知识,这些都易于为普通公众所接受。而19世纪后期以来,一些更为强调审美感性,有意削弱历史叙事和知识性、讯息性的展览则更容易让公众“迷失”,比如在巴洛克美学复兴的影响下,一些博物馆将不同流派、时代的作品并置展陈,标签和说明信息也缺失或十分有限,这样的博物馆常常会进一步加固或“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公众的文化分层。事实上,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说明标签、指示牌、导览手册这样的引导辅助材料其实十分必要,虽然它们不能弥补公众在教育、修养上的不足,但仅仅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消减“无知”的参观者对于自身“无价值”的感受,也能消减艺术品的“遥不可及”之感,甚至还能授予这些观看者某种保持“无知”的权利。
除此之外,艺术博物馆的区隔效应还体现在建筑空间本身。“圣殿”式博物馆神圣、高贵的象征地位在物理的空间形态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除却模仿庙宇、教堂等的外形设计,入口处的台阶常常是关键的建筑元素:这种“拾级而上”的进入方式其实就是对艺术地位的隐喻,它表明艺术高蹈于日常生活之上,“独处于一个唯美的世界中”。“拾级而上”也是欣赏艺术之前的一种“身体仪式”,它将艺术与日常、神圣与平凡、被提升的主体与庸常的主体相区别。除此之外,有人还主张:艺术博物馆主体建筑邻近和周围的区域都应该与“艺术”有所关联,通过喷泉、雕塑和其他有趣对象的设置,“为将要进入博物馆的心灵做好准备”。虽然20世纪的一些博物馆设计都力图打破这种空间区位上的分隔,甚至将艺术博物馆整合进城市规划之中,但就其经典建筑形态而言,艺术博物馆常常与日常生活时空和普通的公共环境有着鲜明的区隔。
(二)区隔理论的局限与公共教育的可能
然而被区隔了的公众就没有流动的可能性了吗?或者说,面对艺术博物馆的区隔效应与其“公共性”理念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与思考能够提供不小的启发。他首先指出,布尔迪厄的区隔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比如过于绝对的二元对立逻辑,以及他在经验研究中对部分证据的选择性盲视。本尼特举例称,如果调查显示喜爱印象主义的专业人士有21%,那么按照布尔迪厄的研究取径,也有33%的专业人士钟爱动作片、惊悚片和冒险片这一事实就会被忽略。可见,布尔迪厄的研究结论部分是建立在主观性选择和不完全归纳基础上的,有其科学性上的局限。
在揭示了布尔迪厄理论的弱点之后,本尼特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立场,这也就是他在论述文化与治理问题时一贯的思路:艺术的审美体制应该与改变生活这一任务相联系,19世纪以来形成的包括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等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虽然不乏区隔效应,却更是“艺术范围拓展的市民管理机构”,应该努力地致力于“训练访客的艺术眼光”。在这种“积极入世”的立场和态度下,本尼特将不同公众间的区隔视作为文化的“斜度”(a normative gradient),而“治理艺术”的任务和功能其实也就是要在体现差异性的文化“斜度”上建立起流动性的关联和可能。
在本尼特看来,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物理空间其实也是一个“示范性”(exemplary)的空间,即使普通公众难以充分理解艺术品,他们也能获得某种“示范”“同化”与提升,这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对公共场合中行为习惯(public manners)的影响。可以说,不同阶层公众的共处为工人阶层和社会大众提供了模仿、效习的机会,中产阶级的行为规范与时尚潮流都可能对普通民众产生示范性的效应。再者,博物馆通过一些禁止性的提示语和观展规范,也能对大众的行为产生约束。此外,通过“通透”的建筑空间、文明肃静的展厅气氛甚至是监控设备等途径,观展的公众也能够自我约束、互相监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共环境下的行为方式与习惯。
虽然这样的“示范”与“同化”作用只是相对浅表和短时的,“自我治理”的“内化”机制涉及更为漫长的过程,然而可以明确的是,艺术博物馆充满张力的“公共性”是它发挥公共审美教育功能的前提:艺术作品与欣赏者之间其实是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艺术品在具有“文化能力”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内被界定,而“文化能力”的培养也要在与艺术品长期的接触与交互中才能实现。因此,如果公众无法与高雅艺术接触,对艺术的解码能力的培养又如何成为可能呢?
更重要的是,与区隔效应并存着的差异性的文化“斜度”,其实恰恰为审美教育和公众的提升提供了动势和契机。因此,用本尼特的话来说,艺术博物馆就“既不是一个简单的同化机构,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别机构:它的社会功能正是被这两种趋势间的张力所界定的。”本尼特的这一论断可谓道出了艺术博物馆“公共性”张力的要义,它也启发我们:艺术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即其公共教育、审美教育功能的发挥,正倚赖于这种独有的张力特征。
三、“定框”:艺术博物馆展览诗学的意识形态
上一节通过对艺术博物馆客观接受效果上区隔效应的分析,反思了其理念、立意上的“公共性”。这一节将从另一个方面分析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其展览诗学中无可避免的话语权力渗透和意识形态色彩。
(一)艺术博物馆的“定框”作用
霍尔曾经联合数位学者围绕“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进行研究,可以说,语言是最重要的表征系统,但这一术语早已不局限于语言学研究领域,而是成为广义符号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重要的理论工具。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一书中,博物馆也被作为表征理论分析的对象。在作者看来,博物馆的表征问题也就是“意义通过分类和展示而被创造出来的方法”,这个通过对展品进行选择、分类、排序、展览,进而创生“意义”的“表征”过程其实就是博物馆展览诗学的“美学加工”机制。学者王璜生联系美术馆的运作实际,将艺术博物馆的表征过程具体描述为展览策划、角度切入、作品遴选、学术支持、空间布置、视觉设计、交流互动等众多环节,并将此称作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
《表征》一书关于博物馆表征问题的章节标题为“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poetics)和政治学(politics)”,具体的论述也从符号学的诗学分析和话语权力的政治学分析这两方面展开。应该意识到,博物馆在对“他者”文化的展览中存在着各种权力甚至是暴力,比如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和解释方式。事实上,欧美博物馆最初的发展其实就与西方的殖民扩张和掠夺行为分不开。因而许多博物馆批评家都将博物馆视作一个“殖民化空间”进行考察。但博物馆涉及的权力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比如历史上艺术博物馆对于女性艺术家的排斥,对于原始艺术进行简单的“美学化”(aestheticization)等等。或许可以说,后现代理论流派中的每一种立场都可以在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实践中找到批评的“靶子”。
因此,以开放后的卢浮宫为早期代表的艺术博物馆虽然一直强调“公共性”这一价值理念,但事实上却始终主导着“立法”和“阐释”的权威,掌握着关于艺术史叙事和艺术品意义的话语权力。甚至可以说,大革命背景下卢浮宫对“公共性”的开启本身就蕴含着建立国家认同的鲜明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
值得指出的是,在艺术博物馆中,“我们看到和看不到什么,以及其中的时段和依据的权威,都与一些更大的问题相关——谁组成了共同体以及谁决定了它的身份认同”。持有不同立场与认同的“立法者”能够建构不同的“公共性”表象,有学者就举例道:德拉克罗瓦主持布置的展厅中不会出现两件不同风格的安格尔作品,而安格尔主持的展览也不会有德拉克罗瓦的画作出现;类似的是,在格林伯格任馆长的艺术博物馆中不会有劳申伯格和奥登伯格的作品,毕加索20岁以后的创作恐怕也不会被展陈。而在意图不同的“阐释者”面前,即使是同样的展品也能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比如一把18世纪在谢菲尔德制作的银质茶匙,在伯明翰城市博物馆中会被分类为“工业艺术”,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Stoke-on-Trent)则是“装饰艺术”,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中是“银器”,在谢菲尔德的凯勒姆岛博物馆中则会被划归为“产业”。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

凯勒姆岛博物馆
对于艺术博物馆这种“立法”与“阐释”的话语权力,美国学者杜若(Paul Duro)曾用“画框”做了很好的类比说明。他指出,物理的画框为画作框定边界,甚至就是它为一幅画作标定了“艺术品”这一身份标记:画框“使得我们将艺术品体验为一种毫无疑问的在场,就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询唤’(interpellate)我们,提供给我们看似独特的观看体验,我们对艺术的期待得到了确认,将其视作超越日常现实的存在”。在阿尔都塞那里,“询唤”这一形象的说法想要表明的是意识形态创造的主体“自由”的表象:个人被“传唤为(自由的)主体”,“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接受这种臣服的地位”。这种“自由”与“臣服”的一体两面性,其实就像subject一词在英语中的双重含义。在这个意义上,画框就起着“艺术(审美)意识形态”般的作用,使人“自然而然”、貌似“自由”地将框中之物确信为艺术,并向其“臣服”。
以此为起点,这样的“画框”似乎可以不局限于原初的物理形制,因而也就有了“机构画框”“知觉画框”“符号画框”“性别画框”“意识形态画框”等变体,它们和物理画框一样发挥着意识形态“传唤”自由主体的功能。就作为“机构画框”的艺术博物馆而言,它“不仅为人工制品定框(enframe),而且为欣赏者定框,它定义了我们的期待,规训了我们的渴望,生产出被我们永恒的在场所统治着的过去和将来”;作为主体,我们为过去确立秩序,并将其组织进博物馆的叙事之中。“定框”这一说法无疑生动形象地揭示了艺术博物馆的权力与功能。
事实上,艺术博物馆“定框”的权威还不仅仅体现在为过去组织秩序、建立起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叙事上,它还可以为“艺术”与“非艺术”划定界限,这可谓艺术博物馆最高的“立法”权。前文提及,丹托曾经以包含“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的“艺术世界”(artworld)理论为艺术定义,迪基(George Dickie)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机构性的要素,认为艺术定义的要素之一是“某种要向艺术界公众呈现的被创作出来的人工制品”,博物馆展览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机构元素。“艺术博物馆本身就是艺术定义的一个框架”,这种使得寻常物品转变为艺术品的“立法”权威还被一些学者称作“博物馆效应”(museum effect):通过将某物从原先的世界中独立出来,用作注视(attentive looking)的对象,创造出视觉趣味(visual interest),进而将其转化为艺术,这其实是在创造一种“观看的方式”。无论采用怎样的理论表述和归纳,艺术博物馆所具有的这种“权力”都是不难理解的。
为非艺术到艺术的转变立法,为展览的诗学表征方式立法,对艺术品进行解释:兼任“立法者”与“阐释者”的艺术博物馆究竟具有怎样的“公共性”,会不会独断专行?在许多艺术创作者心中,作品能够进入博物馆展陈就意味着获得某种承认与肯定,“它便平添了一顶权威的光环”;可以说,“博物馆代表社会的利益来认可艺术”,为某些作品赋予艺术的权威,进而将其展示给公众。然而作为高雅文化机构的艺术博物馆对于“社会的利益”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呢?丹托质疑道,博物馆体制对“美的艺术”和“实用的艺术”进行二分,它以提升之名,把“美的艺术”从日常生活中分隔出去;而“分类的权力就是统治的权力”,“它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这就像为女性框定“夫人”的身份,规定她们安处客厅那样“野蛮”。因此,在他的“艺术终结”理论中,丹托主张重新消解博物馆“定框”的权威,以适应传统艺术范式本身的“死亡”与转型。
(二)“定框”机制的意识形态特征
值得指出的是,“统治的权力”“政治性”与“野蛮”,这些用词反映的都是批评家们的灼见,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艺术博物馆中的话语与权力常常隐而不彰、难以觉察。博物馆像庙宇、圣殿一样神圣,“庙宇总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它们的精神性实践和它们的主张所掩盖。只要博物馆代表着从美通向真理的庙宇,那么,权力的现实就看不见”。就艺术博物馆展览诗学的“美学加工”机制来说,选定主题、确定展品、策划展览、布置空间等步骤都由“策展人”“专家”或是“委员会”推进,这个建构和组织的过程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可见的。因此,一直以来,“博物馆中主体、客体间的关系被视作是给定的(given)、自然而然的”,艺术博物馆“既存的妆容(make-up)和它涉及的各种刚性关系都被认为是给定的”。公众甘于也惯于做被动的接受者,并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应当、“自然而然”。
这不正是意识形态的运作特征吗?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和阶级社会,它是一套包括形象、神话、观念、概念等在内的“表象体系”,是“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切通过符号系统对实在关系进行的想象性、能动性表征都有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博物馆的诗学表征机制自然也可以成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意识形态通常被认知为既是自然化又是普遍化的”,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话语机制”,将特殊、偶然的事物呈现得似乎“自然而然、不可避免、不可改变”。一旦符号系统的能动性表征机制被“自然化”“普遍化”以后,意识形态就生成了。如此看来,艺术博物馆独具权威却又让公众感到“自然而然”的“定框”作用不正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在《表征》一书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著作中,博物馆的“诗学”机制与“政治学”权力常常被并提,然而细细考究可以发现,艺术博物馆意识形态的“政治”其实是蕴含在展览的诗学机制之中的,展览诗学选择、排序等的“美学加工”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渗透着权力的隐性运作,这也是博物馆“公共性”理念与生俱来的自我矛盾。对此,我们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策略呢?这种“公共性”的内在张力在艺术博物馆发挥审美教育功能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既然“公共性”的张力不可避免,那么就不应该无视它、回避它,而应该积极地面对和利用,建构起一种科学、合理、能够对公众产生有益影响的“博物馆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性交错的复杂语境中,一个具有引导力的“定框”权威理应得到树立,正如学者王璜生所言,美术馆如果不能在其建构起来的艺术史叙事中表达某种知识的立场或文化的信念,那将是失败的、没有尽到责任的美术馆。
其次,一种“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式的自我解构、自我反思机制应该在艺术博物馆的展览诗学中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博物馆的“美学加工”机制应该暴露、呈现给公众,甚至使公众有机会参与其中。这种具有“自反性”(reflexive)的博物馆模式被称作“后博物馆”(post-museum)或“超博物馆”(extra-museum),它们在西方已经开始了实践。“透明性”和自反性机制的加入可以有效地牵制“定框”权威的独断性力量,防止出现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暴力。这些都是艺术博物馆在面对“公共性”张力的同时发挥其公共教育功能的策略所在。
四、“公共性”的实践:艺术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
前三节的分析分别揭示了艺术博物馆有别于私人收藏的“公共性”,这一理念上的“公共性”在客观效果上的区隔效应,以及“公共性”宣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此前的论述也已经明确了应有的立场:艺术博物馆的“公共性”虽然充满矛盾和张力,但依旧是其发挥审美教育、文化治理功能的可能性与前提所在;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艺术博物馆应该面向公众、接纳观众,发挥合理的“定框”作用,进而引导公众成为自我提升、自我治理的主体。这里希望进一步论述的问题是:在审美教育的实践中,艺术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张力和距离应该维持在怎样的合理限度上。
2014年6月,在上海市淮海路K11购物艺术中心举行的莫奈画展落下帷幕,虽然票价高至百元,但观展场面异常火爆,甚至要排队才能进入。相比之下,同期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鲁本斯展颇显“身段”,而且票价低廉,但观众却远不如莫奈画展中的那么热情。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很多,学者王国伟认为,K11的“亲和力”与中华艺术宫的“距离感”是其中的关键:位于市中心的K11能够让观众来去自如,毫无“生理负担”和“心理负担”,而“中华艺术宫的体量太大了”,其中的空间设计、展览布置常常令人产生“心理距离”和“迷失”感。此前,莫奈画展的主办方也曾在中华艺术宫举办过毕加索艺术大展,却和这次的鲁本斯展一样遭受冷遇。
这样的归因未必绝对正确,却颇具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此前对艺术博物馆区隔效应的分析中,许多引述都表明了普通大众在艺术“圣殿”中可能感受到的“无知”与“迷茫”;而通过莫奈画展和鲁本斯展的对比还能看到,即使是官方支持下乐于接纳公众、致力于公共教育的艺术博物馆,仍可能使大众产生距离感。这种心理上的“距离感”未必仅仅源自公众无法理解艺术的迷惑,更多的还可能是源自他们在接近、理解艺术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与“负担”,这也就是“体量太大”的中华艺术宫为学者所批评的问题所在。
这种艺术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所产生的压力,正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样:人们进博物馆时总觉得像是走进国王的宫殿,“屈尊俯就地打开后让他们胆战心惊地看上一眼”;博物馆空旷、寂静、恢弘的环境令人敬畏,因而“根本无需博物馆方面去劝说他们不要待得太久”,公众在这种气氛的“压迫”下就很可能很快离开。经典的“圣殿”式博物馆建筑精心设置的抬升性台阶、与周边日常环境的区隔等,都强化了这种艺术的“距离感”和艺术欣赏时的“压力”氛围。

中华艺术宫
除此之外,“体量太大”的中华艺术宫也能使公众感到疲惫,有博物馆研究者将此称作“画作过量”或“博物馆过量”,这种情况下过于丰富的展品只会给人造成纷杂迷乱的印象,并不利于静观沉思的审美体验。贡布里希也认为:“庞大而拥挤的博物馆的参观者很容易遭受到的混乱、疲惫甚至眼花缭乱,其真正来源与其说是物品的众多,不如说是迷惑感”,而即使是一些经验丰富的参观者也难以摆脱这种主观感受上的困境。为此,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减少体量、分散布置的设想:“如果一次看了太多东西让参观者在身心两方面都感到疲惫不堪,那么在城市不同地区办几个规模小一点的博物馆是否要比一个规模巨大、收集了大量藏品的博物馆更好?”这种分散性地融入城市机体,更为轻巧、亲近的艺术展览模式正是私人画廊、商业艺术中心等有别于公共艺术博物馆的优势所在,这或许也就是K11在莫奈画展中赚足人气的一大缘由。
在《博物馆与饥渴的大众》中,丹托深切地意识到,既有的艺术博物馆并不是无数饥渴的民众真正渴望的东西,它们只是人们“童年的记忆”“东帕克道的一个建筑物”,并没有给大众当下的生活带来特别的意义。然而民众们又确实是饥渴地“渴望艺术”,无奈既有的博物馆无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饥渴的大众”苦苦寻求的是什么呢?丹托说,那是“一种他们自己的艺术”。所幸的是,当代的艺术博物馆正在不断寻求更能亲和公众的呈现方式,比如上文简单提及的“后博物馆”,它们将公众纳入到策展等“定框”权威的协商共治之中。又比如一些现代艺术博物馆取消了台阶设计,使入口与马路持平,这和附近的写字楼相比变得毫无差异。
而更能亲近公众、吸引公众甚至是有迎合大众之嫌的,是晚近的“文化综合体”式的博物馆。通过休闲娱乐、餐饮购物等功能与艺术欣赏的整合,通过对大众文化机构的仿效,艺术博物馆在审美体验之余创生了更多的感官愉悦,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因而就其功能定位而言,艺术博物馆除了作为精英化的艺术殿堂和实用主义的公共教育工具,还能成为“休闲产业”、大众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晚近艺术博物馆空间中艺术品“观看者”(spectator)与“游客”(tourist)之间产生了身份张力,这也是参观博物馆的公众虽然身在其中但事实上仍与艺术遥遥相隔这一“距离”感的悖论。
无怪乎有论者感叹,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可谓异常复杂。一些策展人认为,艺术博物馆只应向那些真正“懂”艺术的人敞开大门,但这样的话就会与“公共博物馆”的定位相悖。而在坚持“公共性”立场的前提下,艺术博物馆又要努力减小与公众的心理距离,避免产生影响艺术欣赏效果的“压力”与“迷惑感”。但是,难道吸引众多“游客”的“文化综合体”式的博物馆就代表了与公众之间的理想距离吗?显然不是。艺术博物馆要发挥审美教育的功能,就必须坚持一定的精英立场:只有差异和文化“斜度”(gradient)的存在,才有教益和提升的空间。如果艺术博物馆一味追求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产业化和大众娱乐功能,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被贬损了。正如学者所言:博物馆“不要去尝试不该是它做的事”,“它不能以牺牲完整、真诚和完美的自由及和谐的统一为代价”,这指的也就是要保持前文引述过的贡布里希所谓的“不画蛇添足的能力”。
回到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来。2008年起,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全国的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机构陆续向公众免费开放,这无疑在经济上为普通市民消除了可能的准入“门槛”。然而面对一个物理空间和准入权限上都极少限制、极具“公共性”的艺术展陈空间,普通大众真的乐意、乐于进入吗?即使置身其中,他们是会沉醉于艺术世界还是会“迷失”,抑或是“娱乐至死”?
曾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曾经提到,上海美术馆免费开放之初,首日就吸引了两万多人参观,博物馆被挤得水泄不通,管理人员也忙得不可开交。但事实上,很多市民只是进去“转一圈”就走了,有的还没进门就折返了,“人们只是听说免费,在免费的前提下进来转一下而已。”因而即使艺术博物馆为公众创造了生理上“零距离”的条件,公众与艺术之间未及消弭的“心理距离”依旧可能颇具讽刺意味地存在着。和K11、中华艺术宫的例子一样,这提醒我们,当代中国的公共艺术博物馆在发挥审美教育、文化治理功能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另一方面,正如本节开始时所提到的那样,在当下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艺术博物馆又不能在另一种意义上过度迎合“游客”,对于其产业化、娱乐化的发展应该保持必要的清醒态度。更重要的是,在一批成熟的、富有布尔迪厄所谓“文化能力”的“公众”形成之前,“定框”的权威和精神教益的力量仍是必要的,艺术博物馆与“大众”之间应该保持距离的张力和提升的空间,而“后博物馆”等策略的适用性也值得思量。总之,“‘民主化’或多元诉求,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扁平化和世俗化”,中国艺术博物馆的发展及其审美教育、文化治理功能的发挥,应该稳步探索。
(图片来源于澎湃新闻及网络,侵删。)